作家手稿如同雕刻家的工作间
【作家手稿观察】
作者:郭洪雷(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汪曾祺一向看重小说语言。他曾经引用苏联作家巴甫连科的一句名言“作家是用手思索的”,用以强调作家只有不断地写,才能“扪触到语言”。其实,巴甫连科这句话,很容易让人推想出另一层意思:不同于印刷文本,手稿留有大量勾改涂画,这些“思索”痕迹,更能反映小说文本发生的具体过程,直接呈现作家思想、情感的细微变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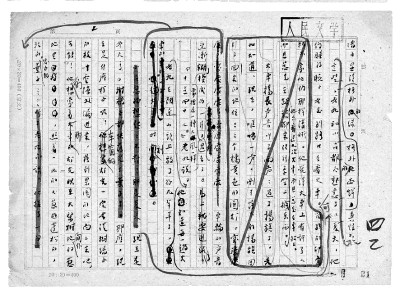
图片为汪曾祺《羊舍一夕》手稿选页。选自《羊舍一夕:汪曾祺手稿两种》
这层道理,西汉扬雄在《法言·问神》中早有论及:“通诸人之嚍嚍者,莫如言。……传千里之忞忞者,莫如书。”这里,“嚍嚍”指愤愤之情,“忞忞”指理之难明。也就是说,语言文字及其书写形态可以“通情”,能够“达理”。所以,扬雄将“言”视为“心声”,把“书”看成“心画”。在手稿中,“心声”“心画”透于笔端,阅读作家手稿可以直抵书写者的内心世界,直观思想和情感变化留下的印记,有效还原其创作思维的原初状态。
金城出版社新近推出、由李建新汇校的《羊舍一夕:汪曾祺手稿两种》,让读者得以窥见《羊舍一夕》和《寂寞与温暖》手稿“全豹”。《羊舍一夕》的手稿是初稿,完整保留了作者修改及相关编校信息,对写作和研究极具参考价值。《寂寞与温暖》是第三稿,手稿本身改动不多,但内容与初刊本有很大不同,此中变化反映着作者的修改策略和文体追求。
汪曾祺经常建议青年作家研究老作家的手稿,仔细琢磨他们改动的地方,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。他还举鲁迅《眉间尺》中的一句话为例:“他跨下床,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,摸到钻火家伙,点上松明,向水瓮里一照。”手稿中“走向”起初写的是“走到”,而“摸到”原为“摸着”。汪曾祺认为鲁迅改得比原来好,特别是“摸到”比“摸着”好得多。这样改,避免了“借着”与“摸着”、“走到”与“摸到”之间可能形成的重出相犯,而且“摸到”只表动作结果,“摸着”还意味着动作状态,鲁迅的改动增强了语言的准确和流畅。细读汪曾祺自己的两篇手稿,辨析勾画、涂抹、增补、删减及删减后的恢复,在推敲与裁夺、犹豫与果决之间,读者可以充分领略他的语言感觉、写作技巧和文学观念,认识他身处人生低谷依旧关注现实、积极融入时代的创作态度。
除一般性订正错讹,两篇手稿的改动大体可分四种情况。首先,与鲁迅对《眉间尺》的改动相近,汪曾祺追求语言的准确。汪曾祺认为:“语言的唯一标准,是准确。”而所谓“准确”,具体来说,“就是把你对周围世界,对那个人的观察、感受,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词儿表达出来”。《羊舍一夕》写小吴对“官中”树剪子的感觉,定稿是:“这不带劲!‘官中’的玩意总是那么没味道,而且,当然总是,不那么好使。”手稿中“这不带劲!”被划掉又恢复,第一个“那么”之后被反复涂改,能辨认出来的就有“乏味”“没味道”“不带劲”等词。“乏味”语意过重,“不带劲”前边用过,反复斟酌后才恢复为“没味道”。再如,写放羊回来的路上可以吃桑椹,原来写的是:“吃得嘴唇、牙齿都是紫的,真过瘾!……”手稿先是在“嘴唇”后加上“舌头”,又涂掉,改补在“牙齿”后面。这样改,呈现了由外向内的观察顺序,显然比原来准确得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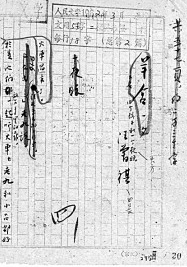
图片为汪曾祺《羊舍一夕》手稿选页。选自《羊舍一夕:汪曾祺手稿两种》
此类改动的更高要求是贴切。这里“贴切”是指“要贴到人物来写”。这句话来自沈从文,意思是作者的笔要紧紧地靠近人物的感情、情绪,不要游离,不要置身人物之外。例如,《羊舍一夕》中留孩喜欢场子,但说不出场子怎么好。作者以代言方式替留孩罗列理由,其中一条的原文为:“这里有电影,两个星期就放映一回,常演战斗片子,捉特务。”手稿中“战斗”被圈改为“打仗”。普通而言,“战斗片子”也说得过去,但有此一改,才称得上“贴切”,真正做到了“人有其声口”。此外,《羊舍一夕》主要写孩子们的故事,手稿原有大段涉及旧戏的内容,考虑到与孩子的意趣贴近度不够,除少许情节需要外,大部分都被删掉了。
其次是调整字句的位置和顺序。汪曾祺说过,小说语言没什么奥秘,无外乎“声之高下”与“言之长短”,只要调配得当,便能产生好的效果。他以王安石给人改诗为例,原诗为“日长奏罢长杨赋”,王安石改成“日长奏赋长杨罢”,并说“诗家语必此等乃健”。他认为小说不必写王安石那样的句子,但要能体会何为“健”,体会出峭拔、委婉、流利、安详、沉痛等言语效果。
《羊舍一夕》里有这样一句话,原本写成:“羊群缓缓地移动,远一点看,像一片云彩在缓坡上缓缓流动。”手稿里前边一个“缓缓”先被涂掉,换成“慢慢”,又被涂掉,恢复为“缓缓”;“移”字前加“往前推”;“移动”的“动”字、“一点”、“缓坡”的“缓”和后一个“缓缓”均被删掉。此句最终定为:“羊群缓缓地往前推移,远看,像一片云彩在坡上流动。”改后较原句远为妥帖,富于动感,且长短参差,变化有致。细辨调整过程及句子周边的涂改、增补,文思的迁转、翕动跃然纸上,仿佛触手可及。小说写放羊人吃肉,只有一种办法,即“把打住的野物用”。写到这里,汪曾祺好像突然找到了最佳句式,马上涂掉这句,写为:“和点泥,把打住的野物糊起来,拾一把柴架起火来,烧熟。真香!”涂改、调整后的语序,一下子就把放羊人吃肉方式的独特性凸显出来了。
再如,《羊舍一夕》写小吕的成长。刚开始是这么写的:“小吕在农场里已经长了一年,他又大了一岁了。他在菜园干了半年,后来调到果园,也都半年了。”初刊本这句被改成:“小吕已经在农场里长大起来了。在菜园干了半年,后来调到果园,也都半年了。”手稿原文略显重复、啰唆,除文字的删减、改动外,汪曾祺还用铅笔勾换了“在农场里”和“已经”的前后位置。如此处理显然与后一句强调时间有关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,汪曾祺讲究小说语言的声韵、节奏,有些地方就像后一个例子那样,只是简单一勾,调换字、词、句的前后位置。这种变动全凭直觉,外人甚至说不出其中的道理。
再有就是追求语言的简单、含蓄。《寂寞与温暖》写沈沅经历变故后的落寞:“不上谁家去剁馅儿,包饺子。也不像一般女同志有打不完的毛线活。”这句话有很多细节,但斟酌再三,汪曾祺还是划掉了,改为“不参加婚丧庆吊,不跟人来往。”改后的句子“刀切水洗”,直截了当。
《羊舍一夕》写丁贵甲的木讷,不灵透,原文有许多吃、穿、干活、发言的细节,后都被红笔涂掉,只剩下很简单的三句话:“小伙子一天无忧无虑,不大有心眼。什么也不盘算。开会很少发言,学习也不大好,在场里陆续认下的两个字还没有留孩认得的多。”这样处理留出了余地和大量空白,让读者去想象填补、思索判断。
汪曾祺叮嘱青年作家要用普普通通、人人能说的话去写,但语言的普通、平淡、日常不等于寡淡,而是要写出味儿。他还强调写小说要讲含藏,要有暗示性,不宜点题,作家的倾向性,应表现于字里行间。《羊舍一夕》写三个孩子煮“高山顶”,烧山药。手稿中汪曾祺先是勾补一句:“他们自己开小片荒种得的。”后又涂掉,改为“——他们在山坡上自己种的。”这里深藏的历史讯息是:《羊舍一夕》写于1961年11月。当年3月,国家出台文件鼓励“小片开荒”,前一句直接点出“开小片荒”,汪曾祺大概觉得有些直露了。
此外,创作观念与时代要求的磨合也是手稿修改的重要动因。1988年,汪曾祺就同时提到这两篇小说,认为它们都带有“浪漫主义”的痕迹,并说自己过去不知道怎样做到“两结合”,后来忽然悟通了:“你不能写你看到的那样的生活,不能照那样写,你得‘浪漫主义’起来,就是写得比实际生活更美一些,更理想一些。我是真诚地相信这条真理的……”在汪曾祺看来,特殊困难时期,书写生活中的美好和理想,让读者感受到“阳光照煦”,比一味关注苦难更有意义。所以,手稿删掉了大段对寒苦生活的书写。当然,过于直露、过于理想的文字,也被他圈改重写了。
细读汪曾祺两篇小说手稿,我们就像走进了雕刻家的工作间:雕凿痕迹随处可见,边角废料纷披杂陈。这不免让人想起他评说沈从文的话:“他的语言是朴实的,朴实而有情致;流畅的,流畅而清晰。这种朴实,来自雕琢;这种流畅,来自推敲。”其实,这些话说的也是汪曾祺自己。
- 2025-08-18十四岁少年的真
- 2025-08-18《庆阳历史文化大观丛书》出版发行
- 2025-08-18长篇历史小说《红玫瑰》首发
- 2025-08-18《一切从童年开始》系列图书:一套心灵成长指南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
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
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
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
今日头条号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