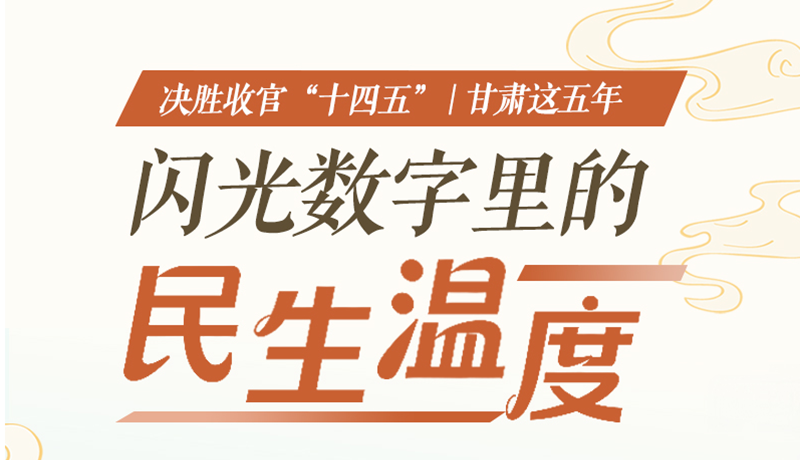富有生命律动的笔痕墨迹 敦煌汉简书写中的生命之流

在浩瀚的敦煌学研究中,那些从流沙深处苏醒的汉代简牍长久以来被视作历史与文字的“化石”。它们承载着边塞戍卒的日常、驿传的律令、商旅的账簿,却少有被以艺术之眼凝视。李逸峰教授的新著《适时与趋变:敦煌汉简书写研究》正是以书法艺术为棱镜,重新折射出这些千年墨迹的璀璨光芒。书中将敦煌汉简称为“字体演进的天然实验室”,这种比喻揭示出作者对书写动态本质的深刻把握。这不仅是填补了敦煌学与书法史交叉地带的重要空白,更是为理解中国书写艺术发展提供了一把新钥匙——书写不是僵死的技艺,而是活生生“适时与趋变”的生命历程。
李逸峰在书中开创性地重构了汉简书写的“动态情境”。他拒绝将简牍文字从生成土壤中剥离,而是将目光投向其书写材质、空间布局、具体功用及书写者身份构成的整体情境中。简牍之“细狭”对书写者构成挑战,却也在限制中催发了章法上的奇巧:字距疏密、行气贯通、大小错落,无不体现着书写者的即时调度。这种“因材制宜”的智慧,正是书者与媒介之间动态对话的明证。
“适时与趋变”这一核心观点,如一条金线贯穿全书,照亮了汉简书法演进的内在逻辑。李逸峰敏锐捕捉到敦煌汉简中隶书作为“主流正体”所经历的日常书写之“蚀变”。在戍卒仓促的记录、驿吏迅疾的抄传中,隶书端庄的波磔被简化,笔画间的映带开始显现,一种“草化”的萌芽悄然涌动。书中对悬泉置遗址出土邮驿文书的分析极具说服力:在紧迫传递需求的驱动下,书写速度加快,笔画的连贯性增强,甚至出现了明显的省简与连笔,这正是隶书向早期行书、章草嬗变的鲜活现场。李逸峰指出,这种“趋变”并非消极的潦草,而是书写者为适应实用效率,在无意识中推动字体演化的积极创造。
该书最富洞见之处在于揭示出敦煌汉简书写中“日常性”所蕴含的力量。书中描绘的书写者——边塞的戍卒、驿站的吏员、往来的书佐——大多不是青史留名的艺术家。他们执笔,只为记录传食、传递军情、抄录律令。这种“急就”的书写状态,剥离了庙堂碑刻的刻意庄重,袒露出最本真、最富有生命律动的笔痕墨迹。一枚习字简上戍卒略显稚拙却充满尝试意味的笔画,在书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,它不再是“技法不精”的证明,而成为“书写练习”这一日常行为本身的珍贵遗存,是普通人参与字体演进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生动脚注。正是这种源自生活、服务于生活的“日常书写”,以其未经雕琢的蓬勃生机,成为书法艺术长河中最为活跃的变革之源。
《适时与趋变》在方法论上的自觉与创新尤为值得称道。李逸峰教授在书中构建了“情境还原—形态分析—书写机制推演—艺术价值提炼”的严密研究链条。他不仅精研墨迹形态的细微差别,更能穿透字形表象,去揣摩那持笔之手背后的“动作思维”:为何在此处顿挫?为何在彼处疾行?为何如此省略?这种对“书写性”而非仅仅“完成态”的执着追问,使得其研究超越了静态的风格描述,触及了书法作为“时空艺术”的动态本质。
李逸峰的研究不仅照亮历史,更为当下书法创作提供了深刻启示。敦煌汉简的书写者身处特殊环境,面对简牍形制的约束与书写效率的要求,他们以“适时”的智慧创造出充满生机的字体流变。今天的书法家同样身处纷繁复杂的文化语境,面对现代展览机制、多元审美需求以及数字媒介的冲击。汉简书写者那种立足当下、尊重媒介、大胆应变的“趋变”精神,对当代书法家具有强烈的示范意义——真正的传承并非对古法的亦步亦趋,而是秉持其内在的创造精神,在当下语境中勇敢探索新的笔墨语言与表达可能。
李逸峰教授在书末将敦煌汉简喻为“活化石”,这一命名充满深意。它们之所以“活”,正因为其墨迹中凝结的并非僵死的程式,而是书写者面对具体情境时那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“适时”应对,以及由此驱动的生生不息的“趋变”洪流。《适时与趋变:敦煌汉简书写研究》不仅是对一段书法史空白的出色填补,更是对“书写何为”这一根本命题的深刻叩问。
当我们凝视这些两千年前的墨痕,看到的不仅是字形的古拙,更是书写者在特定时空限制下迸发的创造力。李逸峰以其精湛研究,让我们听到了敦煌流沙之下那奔涌不息的书写生命之流——它穿越时空,依然在叩击当下每一位执笔者的心灵。
田文倩
- 2025-11-18甘肃籍导演张忠获白俄罗斯总统奖
- 2025-11-18奶皮子糖葫芦刷屏金城 30元一串的爆款,是味觉革新还是“社交税”?
- 2025-11-18甘肃省区域公用品牌“陇上好粮油”上榜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
- 2025-11-18让嘉峪关真正成为“游客值得来的地方”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
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
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
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
今日头条号